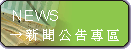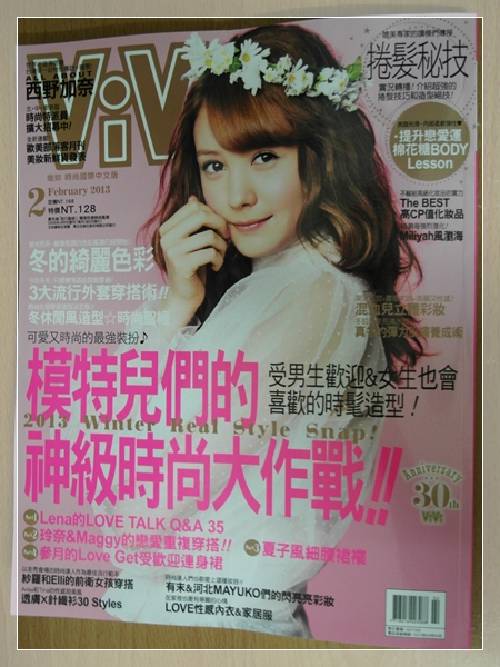遠方的鼓聲為誰而響
遠方的鼓聲為誰而響 
村上春樹的《遠方的鼓聲》(編按:指日文版,以下同),是我擁有的第一本村上春樹的作品。它的特別之處,是我在紐約街頭從黑人街友手上買來的。
1994年有段時間,週一到週五我必須天天從紐澤西的住處搭公車到紐約曼哈頓四十二街的公車轉運中心,再走幾個街口,穿越百老匯大道的歌舞劇戲院到洛克菲勒大樓上班。那時候,紐約的治安大幅改善,常會看到警察穿著深藍制服騎著駿馬或開著警車巡邏,即使一個人行經路旁不時有街友留連的四十二街情色店區也不會讓人心神不寧。不過因為路上多是趕著通勤的上班族,每個人臉上都行色匆匆。
那一年某一天,在四十二街街頭,一位黑人街友的二手書攤卻吸引了我的注意。在眾多英文書刊雜誌中,夾雜著一本日文書,突兀而顯眼。我停了下來,把那本平裝書展開,書皮雖然有點磨損,但內頁幾乎是全新的。黑人街友不知從哪裡撿來這本書,總之他顯然完全不懂日文,用鉛筆在書末空白頁寫著兩塊錢,但是那個「2」和書籍的文字排列方向上下顛倒,反了過來。那時候我只懂一點點基礎日文,只看得懂書名及作者,並不比黑人街友好多少,也沒資格說人家。
你一定知道了,那本書,就是《遠方的鼓聲》。
因為才兩塊美金,我便買下了它。其實,我那時候對日本當代文學並不熟悉,還沒聽過村上春樹、村上龍、吉本芭娜娜……等人的大名,更不曉得「村上春樹」的日文讀音。只是從書名《遠方的鼓聲》隱隱感覺到一股心靈的騷動。遠方的鼓聲,是什麼樣的鼓聲?為何而響?為誰而響?總之,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買下它。若再深入細想,或許那時一直覺得自己是陰錯陽差來到紐約,心中更嚮往的則是繼續深造,研究日本文學。
總之這本從黑人街友手上買來的《遠方的鼓聲》,在1999年底跟著我從紐約千里迢迢回到了台灣定居。但直到我重新展開學生生涯,轉換領域攻讀日本文學、比較文學之後,我的恩師林水福教授建議我做村上春樹研究,我才真正有機會打開它,一字一句地讀下去。後來,我有幸與藤井省三教授進行共同研究,並經他本人指名由我翻譯他的大作《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有次曾對藤井教授提起這段「在紐約向黑人街友買來《遠方的鼓聲》」的我的村上春樹初體驗,被藤井教授詮釋為這是冥冥中的宿命安排,是屬於我的一段「legend」。
好了,閒話休提,言歸正傳。《遠方的鼓聲》這本書,是村上春樹和太太陽子於1986年10月到1990年1月旅居羅馬、希臘期間寫下的散文札記,出版於1990年。中文譯本《遠方的鼓聲》直到2000年才出版。在村上春樹旅居歐洲這段期間,還交出了《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兩部長篇小說稿件,以及一部提姆.歐布萊恩的《核子時代》譯稿,還有,一篇短篇小說〈電視人〉。
這段在希臘生活的經驗,蘊育出短篇小說〈吃人的貓〉(注),後來成為《人造衛星情人》的部分情節。我認為,〈電視人〉、〈吃人的貓〉、《人造衛星情人》的某些構思,就是2009、2010年大暢銷的《1Q84》中「little people」和「貓之村」的原型。例如在〈吃人的貓〉中,人夫男主角因和人妻女友的外遇曝光,兩人各自離婚帶著所有積蓄飛到希臘小島生活。後來,女友和貓都神祕消失,只聽見遠方的鼓聲樂聲不斷響著。而主角自己也消失了兩次。
在主角和女友搭機飛往希臘時,「突然間我覺得自己好像消失了……坐在飛機上的那個人已經不再是我了。」而當主角在希臘小島上找尋消失的女友時,「沒有任何預兆地,我不見了。也許是因為月光,或者是因為半夜的音樂,每踏出一步,我就感覺到陷入流砂中,愈陷愈深,在那裡我的本體消失了。」這情節,是不是跟《1Q84》那個青年消失在「貓之村」有相互呼應之處呢?甚至,對應到當時我在紐約的感覺,是不是某方面來說,我也在紐約消失不見了?
拙作〈有了4 Books,何需Book 4〉(《聯合文學》2011年10月號)曾指出,《1Q84》中天吾與青豆的故事,或許從來就不是「純愛故事」,而是「自己」與「自我」的故事。青豆只是天吾正在寫的小說中的人物,而天吾真正在尋找的,就是「我的本體」。由於篇幅所限,在此僅舉出天吾的「空氣蛹」裡是十歲的青豆,就能夠提醒讀者青豆就是天吾的「心之影」。重點在於,天吾藉著《1Q84》的故事,重拾當年解救被同學霸凌的十歲的青豆的那個主動與積極的自我。而那也就是尋回消失的我的本體的故事。
扯遠了。如今,「在紐約向黑人街友買來《遠方的鼓聲》」這段經歷,轉眼也成了將近二十年前的往事,現在悠然在腦海響起,成了不折不扣的「遠方的鼓聲」。儘管研究村上春樹已經十年了,我還是不敢稱呼自己是村上迷,但隨著愈來愈熟稔,村上各個時期的作品,時時鼓動我的耳膜,成為我的自我的一部分,提醒我勇敢朝向未知前進,不要輕易消失不見。
引用:Yahoo!奇摩新聞
Yahoo!奇摩圖片
--------------------
產品推推